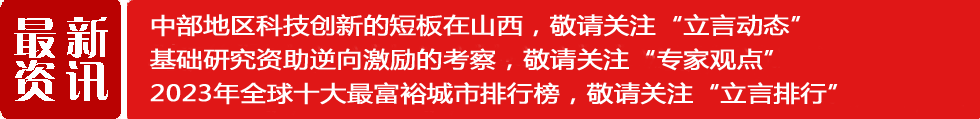
|
||||
|
||||
|
||||
|
||||
美国新产业政策战略的框架和关键行动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2022年5月发布报告《重启美国新产业政策的框架》(Reboot:Framework for a New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报告认为,在当今这个以技术为中心的战略竞争时代背景下,为了有效应对中国挑战、增强和延续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世界技术领先地位等,美国亟需制定全面、长期、统一、前瞻的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报告居然将“应对中国的挑战”列为美国需要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的主要理由,值得警惕!报告提出了美国新产业政策战略的框架和关键行动。
在美国宣称美中竞争已经进入“极限竞争”时代、并不断加剧美中全面战略对抗的氛围和手段的背景下,有必要密切关注美国产业政策战略的调整动态,特别是在美国政府不断推行和持续强化其“友岸合作”的各种联盟政策和“友岸外包”的产业链供应链政策的各种新的竞争手段情况下,需要以有效的产业政策保障产业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自立自强,促进和保障我国产业链的先进性、稳定性、独立性和安全性。
报告认为,美国自建国以来虽然实施了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但多是以零打碎敲的方式来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且近30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导致国家对私营部门创新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私营部门却无法提供国家利益所需的全部创新。为应对现实的国际挑战,加强关键产业的创新和制造能力,美国政府必须在国家新产业政策战略的指导下,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具体的重要产业活动中。
报告阐述了美国需要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的理由、梳理了美国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并提出了执行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需采取的关键行动。
一、美国为何需要新的国家产业政策
1.应对中国的挑战
报告声称,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战略竞争。中国已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挑战”。而关键技术(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科学等)的发展、控制和使用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技术具有促使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潜力。报告指出,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时面临着以下不利条件:
(1)美国的研发支出在不断下降,相对优势在不断缩小。美国国家研发支出总额(公共和私人)的全球占比已由1960年代的约70%下降至2019年的27%;而中国的研发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0.72%上升至2018年的2.14%。且2010-2019年间,中国研发支出的年均增长率(10.6%)明显超过美国(5.4%)。据分析估算,至2020年代中期,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会超过美国。
(2)美国的人力资本在不断萎缩。由于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投资的不足,以及限制性、繁琐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的人才基础变得紧张。虽然美国已通过或提出了相关补救性的立法措施,但政府的这些努力仍缺乏一个总体国家战略。
(3)中国已实施了一系列广泛影响全球市场的国家产业政策。
例如,“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军民融合战略”、“中国标准2035”、“双循环战略”等。这些产业政策已经对全球市场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2.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制定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为了增强美国竞争力,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繁荣、加强国防实力并应对社会挑战。新的产业政策战略应该横跨国内产业与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范畴,为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提供连结组织。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不仅要能用以解决从应对气候变化、改革基础设施到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等的一系列问题,还要能够为决策者提供解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目标重叠问题(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使两者日渐趋同)的路线图。
二、美国国家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
1.一个工业国家的诞生
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奠定了美国产业政策的基础,开创了早期政府利用投资、关税和补贴来支持私营工业和制造业发展以追求社会发展公共目的的先河。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Henry Clay)于1824年主张拥护保护性关税来支持“一个真正的美国体系”(a genuine American System),以充分保护美国不受外国的压倒性影响;呼吁用美国商品来填补美国空白,并促使《1824年关税法案》(the Tariff of 1824)成为法律。汉密尔顿整合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源的方法,以及克莱的“美国体系”理想,在美国随后的几十年里多次重复出现,最突出的案例是帮助解决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全球危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于1917年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the 1917 War Industries Board);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国家工业复苏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促成了1933年国家复苏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成立;1942年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委员会(the World War II War Production Board)。这些机构寻求促进产业界、劳工和政府在美国制造业、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和分配方面的协调,满足了美国当时迫切的现实需求,并为未来和平时期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
2.科技的新前沿
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是奠定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基础的产业政策的推动者。由于担心美国在二战初期缺乏技术准备,布什于1940年主张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并担任主任,以专注于国防技术的研发。布什后来又担任1942年新成立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任。以上两个机构都寻求召集各类科学专家,以协调和优先考虑政府与大学和工业实验室的研发合同。这种研发合作的目的是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迅速重建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优势,避免了将资源投入到建设更多的国家实验室上。在其1945年标志性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布什继续强调了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其观点激励了美国数十年的研发投资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布什的贡献是帮助美国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新技术出现的创新环境,例如全球定位系统和早期互联网,这些技术仍继续支撑着今天的进步。
3.冷战时期产业政策的起起落落
由布什奠定的研发投资基础,加上强有力的军事建设,使得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技术实力最终超越了苏联。但随着苏联于1957年10月成功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美国各界对美国的滞后深感不安,并正式拉开了美苏太空争霸的帷幕。出于民族自豪感和必要性,美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公众均投入资金以构建专业知识,并加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大幅增加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持。鼓励学生学习STEM,并通过立法来资助学生的STEM和外语培训,如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1958年7月,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随后又成立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用以确保美国是“战略技术意外事件的发起者,而不是受害者”。NASA和ARPA所引领的创新已远远超出了冷战的范畴,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CT)、假肢、隐形飞机和语音识别等技术。这种资源和合作的突然扩张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技术竞争力的新时代。在接下来的30年里,美国政府通过更有针对性的立法继续激励科技发展。例如1980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 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以及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R),实现通过知识产权共享和技术转移框架鼓励产业界和政府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在需要的情况下,美国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产业发展之中,就像1987年美国半导体产业一样。面对日本公司的竞争激烈,美国半导体的全球产量由此前20年的60%下降至1980年代末的不足40%。为了缓解这一萌芽中的危机,联邦政府与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SEMATECH,是一个由14家美国半导体公司组成的财团)合作,并向DARPA提供了约8.7亿美元的资金以用来加强该行业。该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10年内,美国芯片制造业重新夺回全球领导地位。
4.美国近年来的产业政策
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要依靠私营企业来推动技术发展。政府偶尔加大对产业发展的参与程度,用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特朗普政府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和《2020年本土稀土法案》(Onshoring Rare Earths Act of 2020)均表现平平。事实表明,推动实施一个成功和可持续的产业政策,既需要一个共同的国家目标,也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根据其目标部署各种工具和子战略。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5月宣布“操控加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OWS),该行动由国防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共同发起,旨在为联邦政府提供一种快速研发COVID-19疫苗的途径。通过该行动,联邦政府与6家疫苗供应商合作,简化了临床试验,通过《国防生产法》授权在短短10个月内为各种关键疫苗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麻疹疫苗和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则分别耗时10年和43年。“操控加速行动”负责人认为此次成功源于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完成科技创新任务的绝对优先级和充足的资源支持,以及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科学界团结一致的努力。
三、美国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的关键行动
报告指出,为了很好部署和实施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需要美国决策者采取一系列持续且纪律严明的行动,并需要产业高管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报告提出了6项相互关联的核心行动,构成美国新的产业政策战略的框架。
1.美联邦政府发出国家产业政策强力号召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在产业政策上缺乏统一的信号,也没有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使得制定全面立法、优化资源配置和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成为一项挑战。因此,美国总统应该发出强力号召,以明确延续美国经济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的愿景和目标。该愿景应该解释经济安全为何应该被视作国家安全。该目标应该是在不损害价值观或主权的情况下,确保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技术强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2.开展相关战略分析研究以确保产业政策成功
为确保做出明智的决定,美国决策者需要对与技术战略和产业政策相关的投入和进程开展持续监测和评估,需要对哪些政策正在起作用、哪些政策不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起作用等问题进行合理分析。但美国政府目前缺乏胜任这一任务的政府机构。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应该领导对目前相关管理权限及其能力的审查,明确其不足之处,以及实施和评估产业政策所需的财政资源。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和建议,国会应和行政部门合作以支持政府的组织框架,并制定、执行、监督和维护新的国家产业政策。为了衡量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需要定义产业政策成功的标准,并对政策的产出和结果进行分析。因此,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由政府各部门、产业界、社会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负责制定衡量产业政策的相关指标。同时国会应该授权对美国产业政策进行持续研究和分析,并报告相关结果。
3.强化政府和产业界的协同合作
报告指出,公私伙伴关系必须成为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的核心特征。如果本应成为产业政策受益者的私营部门和公司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那么该产业政策就是失败的。美国能将政府的财政资源和目标与产业界、以及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世界一流的科研能力相结合,该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战略优势。在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支持下,白宫和国会应该努力识别出在优先技术领域和科学学科上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机会。每一种伙伴关系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且这些目标应植根于更广泛的产业政策目标。
4.根据需要创建政府管理机构并授权以调整政策
有效的美国产业政策战略应该是动态且适应性强的。根据技术领域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参与产业部门的方式和程度将会发生变化。如何以及何时管理和更新这些产业政策将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分析、评估和协调能力。该项工作十分困难,美国需要新的官方机构和领导能力。因此,总统应该任命一名负责技术竞争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该职位可由一个协调办公室担任,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最高职位,其任务是根据对当前所开展工作的持续分析,为产业和技术竞争政策提出建议。
5.接受并降低产业技术创新风险
政府加大对产业发展的参与和对学术研究的投资力度,也意味着政府需要对失败抱以更大的容忍度。因为科技进步根植于高风险、高回报性研究。降低失败影响的一种方法是采用组合方式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即以资助一系列参与者的方式对所需的能力进行研发投资,从而实现分散风险、从整个投资组合获得净收益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消除繁文缛节并下放决策权限。因此,白宫和国会应该致力于重构监管体系,以支持更加灵活的产业和技术政策的实施。白宫必须信任中层官员,避免微观管理;国会必须提高那些必须由它来直接批准的政府投资的门槛。
6.充分利用盟国及建立科技外交官队伍
美国的产业政策需要开展国际合作。鉴于技术和相关知识的全球扩散,开展国际合作是一个务实的现实,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相形见绌,而这些“民主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从研发投资、标准制定到供应链弹性等领域的合作将增强各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利益。因此,国会应该拨款用于建立一支美国科技外交官队伍。这些官员将是在国际方面执行美国产业政策的先锋队,其工作领域包括合作研究协议、人力资本交流、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管制等一系列方面。
(资料来源:智强战略咨询)


 使用QQ直接登录
使用QQ直接登录








